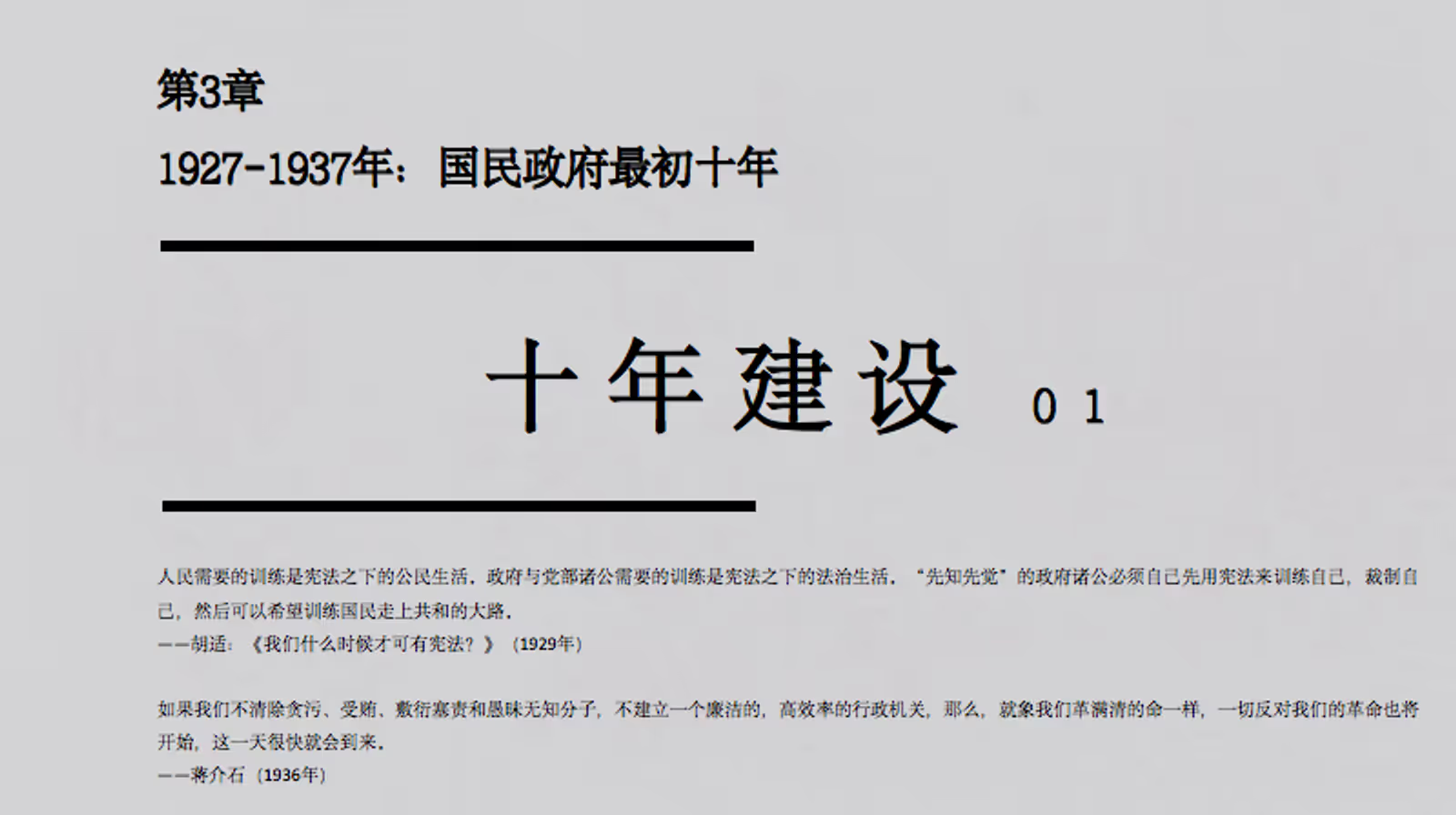
获取了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并于193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何廉(1895-1975)对于北伐胜利之后的中国形势曾有这样的感叹:“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啊——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1]
不过,清党之后,国民党的不少举措因其主要基于维护政权的立场而没有获得好的印象。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觉得他拥有了与中共合作的失败教训,他有他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方法,因此,他几乎是本能地表现出谨慎和小心翼翼。充满激情与革命理想的人不是被怀疑和屠杀就是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留在国民党内的投机主义分子或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者加大了比例,没有人愿意去积极地做具有责任感的工作,国民党的革命性很自然地就减弱了。既然在大屠杀中处死了不少工农中的积极分子,再与工农发生正常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国民党迅速失去了理解并同情自己的社会与民众力量。一方面,为减少军事进程的时间而妥协导致的军阀与旧官僚进入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各级重要位置弱化了党的精神,另一方面像“蓝衣社”这样实施恐怖的组织,也很严重地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色彩减弱,在很多人看来,蒋介石的角色越来越接近法西斯独裁,因为谁反对他及其他领导的国民党谁就是反革命,虽然蒋也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国民党政权有选择性地处置贪官污吏。尤其是,中共揭示国民党并不代表广大的工农群众,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尽管20到30年代的中国的资本家(商人、银行家、工业与一般实业投资者)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或外来资本的挤压[2],这样的形象与中共持续的宣传当然容易激起贫困大众的反感[3]。所有一切,都影响到国民党对政治制度的有效建设——尽管它不断地告诉它的人民:这个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宪政。
尽管矛盾与问题重重,仍然有历史的亲历者——例如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认为从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是国民政府“黄金的十年” (Golden Decade),是中国开始进入现代国家雏形的十年:北伐收获的南北统一使国民政府开始了超过80%领土相对有效的统治。无论如何,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策略为国民政府争取了5年左右的建设时间(1932-1936)。1931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进入国际联盟非常任理事国,在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有了将中国问题放在国际平台上去讨论和解决的条件;现代建筑拔地而起;城市街道和管网以及现代生活的功能在不断完善与丰富——以致人们经常将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形象与生活方式联想到欧洲;甚至那些类似欧洲城市里的装饰物例如建筑雕饰与环境雕塑,都给人一种新的都市生活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也希望通过推动“新生活运动”来展示国民政府在现代化建设时期获得人们认可的路径。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之意义》的演讲,他提倡一种受德国战后秩序影响的新生活运动,初以军事化,次年注重生产,再年融入文化活动。将国民的体魄与身体素质作为现代生活的要求当然受德国的影响,1933年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已经显示了政府在提高国民素质上的努力,彼时所谓“体力即国力”成为响亮的口号,之后,学校中的体育运动获得进一步普及。不过,很难评估这场试图唤起人们崭新生活态度的运动的成绩,既然人们的生活方式被要求合于礼、仪、廉、耻的标准——那时人们将这几个字与英语“礼貌”“公正”“诚实”和“自尊”联系起来理解,就势必使这个以新生活为名的运动的内在资源连带出儒家传统思想的气息——尽管蒋介石是个基督徒。蒋介石甚至号召人们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要去阅读《大学》《中庸》这样的古代经典。5月,国民党甚至通过决议,确定每年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在全国恢复祭孔。这种让人联想到袁世凯的举措激起了知识界的反感。老舍、曹禺、叶圣陶、郑振铎、陈望道和郁达夫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带着嘲讽的口吻批评说:
我们相信复古运动是不会有前途的。假如读经可以救国,那么,“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假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可以救国,那么,李鸿章和张之洞早已成了大功了。时势已推移到这个地步,而突然有这种反动现象发生,我们虽然明白其原因并不简单,但不能不对这种庸妄的呼号,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促其反省。 [4]
这时,人们对十多年前“打倒孔家店”的启蒙运动还保持记忆,在提倡传统道德的同时,国民党也听从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希望通过这样的运动达到提振国民精神、奋力强国的目的。这个从南昌开始,有蓝衣社参与,之后波及全国,大街小巷能够见到“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标语的新生活运动直至1936年结束。
从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直至1935年就任行政院长期间,国民政府的经营者是以孙科与汪精卫为中心的人,国民党四全大会于1931年11月召开,通过了国家建设的基本方针。出于建设的急迫性,国民党提出了“人才主义”的方针,无论党内党外,人才都要广揽,以便国民建设。孙科在四届一中全会的闭幕时说:“必须广揽人才,实行直接民选,实现民主政治。”这种空气使得更多的专门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分布于法律、教育、经济、金融以及交通网络和通信领域,甚至包括出版业,著名的杂志《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22日——尽管这个杂志的重要作者胡适、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等人的立场与中共确也保持了明显距离。
“安内攘外”的政策——主要目的在围剿中共与抵御日军日益严峻的入侵——首先是要充实军事力量与势力。基于与苏联断交,蒋介石国民党开始依赖德国军事顾问来实现自己的建军目标。国民政府先后通过私人合同的方式相继聘任鲍尔(Max Baur)、克里伯(Hermann Kniebel)、魏泽尔(Georg Wetzell)、希克特(Hans Von Seeckt)、福根豪森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国民党围剿中共时,德国顾问团队不同工种专家的人数达到了上百人,先后为国民党的军队培训了30万士兵。正是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一些建议,为国民党围剿的最后成功提供了战术与方法:陆军建立了机械化部队,增加了军械库和陆军医院;除了基于清末就开始建设的海军的发展,空军事业也全面启动:国民政府于1928年在杭州成立航空班,进而于1931年改制为中央航空学校;1936年,在南昌成立了中国航空机械学校。直至1936年,中国拥有各类飞机855架,1937年5月,全国已经有了6个空军区。在军工方面,除了建设工厂,与意大利和德国也合办了军工企业。这些完成于1936年之前的军事事业,为1937年之后的抗战提供了基础。不过,也正是聘用了德国军事顾问,使得始终限于党内派系斗争的蒋介石很容易接受顾问们传递给他的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例如鲍尔上校就参与了德国纳粹运动,他为顾问团所挑选的顾问都与他的思想倾向保持了一致;克里伯本人就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他甚至参与了1929年5月慕尼黑啤酒馆暴动期间的纳粹游行(他被监禁的室友就有希特勒),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有不少中国军官去了德国留学,而那时,正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因此,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之后开始思考组织自己的恐怖组织蓝衣社并让这个组织完全忠实于自己,这样的事实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法西斯纳粹组织对他的影响,尽管蒋介石的目的是想让国民党衰弱的精神和意志重新恢复力量。
外交方面的收获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之后并不明显。“五卅”运动之后,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再次高涨,北京政府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不多。1925年10月26日,中国与英国、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代表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关税自主问题;1926年1月12日,中国又与英、美、日等列强讨论法权问题,这些国家之前对中国司法进行过调查,谓:中国需要改进司法,方能够废除治外法权;1927年1月,比利时声明结束旧约,重新签订平等的新约。1927年1月和2月,中国军民与武汉和九江英军水兵发生冲突,导致最后中国与英国以合同的方式将武汉和九江的租界收回,之后,又陆续收回镇江英租界(1929年10月31日)、威海卫英租界(1930年4月18日)以及厦门英租界(1930年9月17日)。1928年,国民政府继去年7月再次宣布关税自主之后,英国、美国、荷兰、挪威、比利时等十国陆续与中国签署关税新约,直至1930年5月,日本也与中国签署了中日关税协定(之前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太多,但直至1943年,即便中国处于僵持的中日战争,国民政府也最后完成了对历史留下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解除)。1930年2月,国民政府开始在公共租界设立法院,1931年7月,开始在法租界设立中国法院,中国国民开始受中国法律的保护。
法律领域的建设先后由伍朝枢和王宠惠主导,伍主持了《户籍法》《铁道法》《预算法》《小学法》《中学法》《师范学校法》以及《职业学校法》等法律文件的制定。伍朝枢去世(1934年)后,在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王宠惠的带领下,法律界的专家完成了一系列作为现代国家必备的基础法律,例如《储蓄银行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央银行法》《出口税率法》《保险业法》《财政收支系统法》《法院组织法》等。
关税自主的执行时间是1929年2月1日,这很快就增加了关税收入,当年就从1928年平均年关税的1亿2千1百万元,增至2亿4千4百万元,之后因日本入侵而受到影响,但是,关税的年收入均超过3亿,因税率的提高,关税额明显增加。作为主要税种的盐税,从1929年的8千5百万元,增加到1936年的2亿1千8百万元;其他税的收入也是国民政府的来源(这又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社会的税务负担)。国民政府的开支很大一部分是军费:用于应付军阀以及剿共,“9.18”之后,开始为抗日做准备,可以想象,军费的开支很难减少,同时又开始了各种事业的建设,这样,财政赤字的上升无法避免。但是,赤字中的部分也包含未来的收获,例如教育经费从1934年的1300万元,增加至1937年的4200万元,这些支出都具有潜在性的社会收益。在财政金融的整顿方面,即便在财政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力争建立预算制度,这为财政运行的合理化提供了基础。国民政府实现了统一征税体制,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在财政收益上的分歧,国家的统一,实现了这样的目标,这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条件。不过,天灾、局部战乱以及地方基层管理不善以及官员腐败,总是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所以在税制方面,人们获得的反应是不同的。当时的一个日本研究者松村祐次在他的研究著作《中国经济的社会态制》(1949年)里对民国政府30年代的农村有这样的记录:
1927年的革命以后,地主企业家费氏家族的财富迅速减少。这部分是由于其佃户独立性的增加,而另一部分是由于新的国民政府推行的发展计划⋯⋯它突然加重了费氏土地的赋税负担,由于从1931年以后开始的萧条使境况变得更糟了,据张忠仁(音)编撰的一部费氏家史,他们邻近苏州的600亩祖传田产连年歉收,费氏甚至把这些田产中的一部分卖掉来交税,情况仍然不佳,费长生绝望下请求政府没收家族的全部土地来清算他们大量的欠税,但他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他不能压迫其贫弱的佃户交租,一次在1935年又给政府写了一封极感人的长信,但在信寄出之前他就病倒死去了。 [5]
同时,税收制度的具体执行还有太多的复杂性与问题,不仅佃农本身处于很低的生活水平,地主也免不了受基层政府官员和地痞流氓的欺负。不同城市与地区当然也存在有贫富上的不均衡性,但是无论如何,历史遗留的税负也会以变相的方式继续存在,即便北伐时期的临时税并没有因为北伐结束而终止,例如将“整军附加税”更名为“重建附加税”,农村的附加税一个接一个,各地的间接税也层出不穷。[6] 可以肯定的是,赋税以及对税收的滥用——官僚机构的扩张以及贪污——是农民与民众难以承担的负担,以致贫困仍然是普遍的。
注释:
[1] 转引自[美]易劳逸(Ltoyd E.Eastman):《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192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1974)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2] 一位在中国历史现场的日本人这样说:“对现在中国的状况,有人说是革命,又有人说是革命的反面即反动。我认为是革命,是革命的进行时。不过,革命也是各种各样,现在正在进行的中国的革命仅限于国内问题,与距今150年前的法兰西革命性质相同。因此,革命的主体是新兴的资本家阶级,这一资本家阶级现在正在上海以鲜明的形态成立。上海之外很少。” (橘朴:《上海财阀共产党冯玉祥》《新天地》1927年7月,本书转引自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这位现场观察者的意思是,上海的资本家阶级是新兴力量,因此,它需要与政治势力结合起来以保证自己能在和平而不是战乱的环境中从事经营,他们支持修订关税并避免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的资产阶级要争取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立同盟的原因,显然,它也是国民党摆脱对俄国财政的依赖进而巩固政权的金融来源。
[3] 埃德加·斯诺在进入苏区询问那些孩子为什么要参加红军有这样一段对话: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
“还有呢?”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么什么叫资本家?”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
[4] 《晨报》1934年8月26日。本书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70页。
[5]转引自[美]易劳逸:《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37页。
[6] 甚至连蒋介石也抱怨:“政府开支持续上升。任何一项计划开始都要举办新税,附加税经常因需要而成为固定税,各种杂税也被创造出来,有时(地方政府)随意向每户征收无名目的税,结果税项极多,人民在这种重税压迫下苦不堪言。” (转引自[美]易劳逸:《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