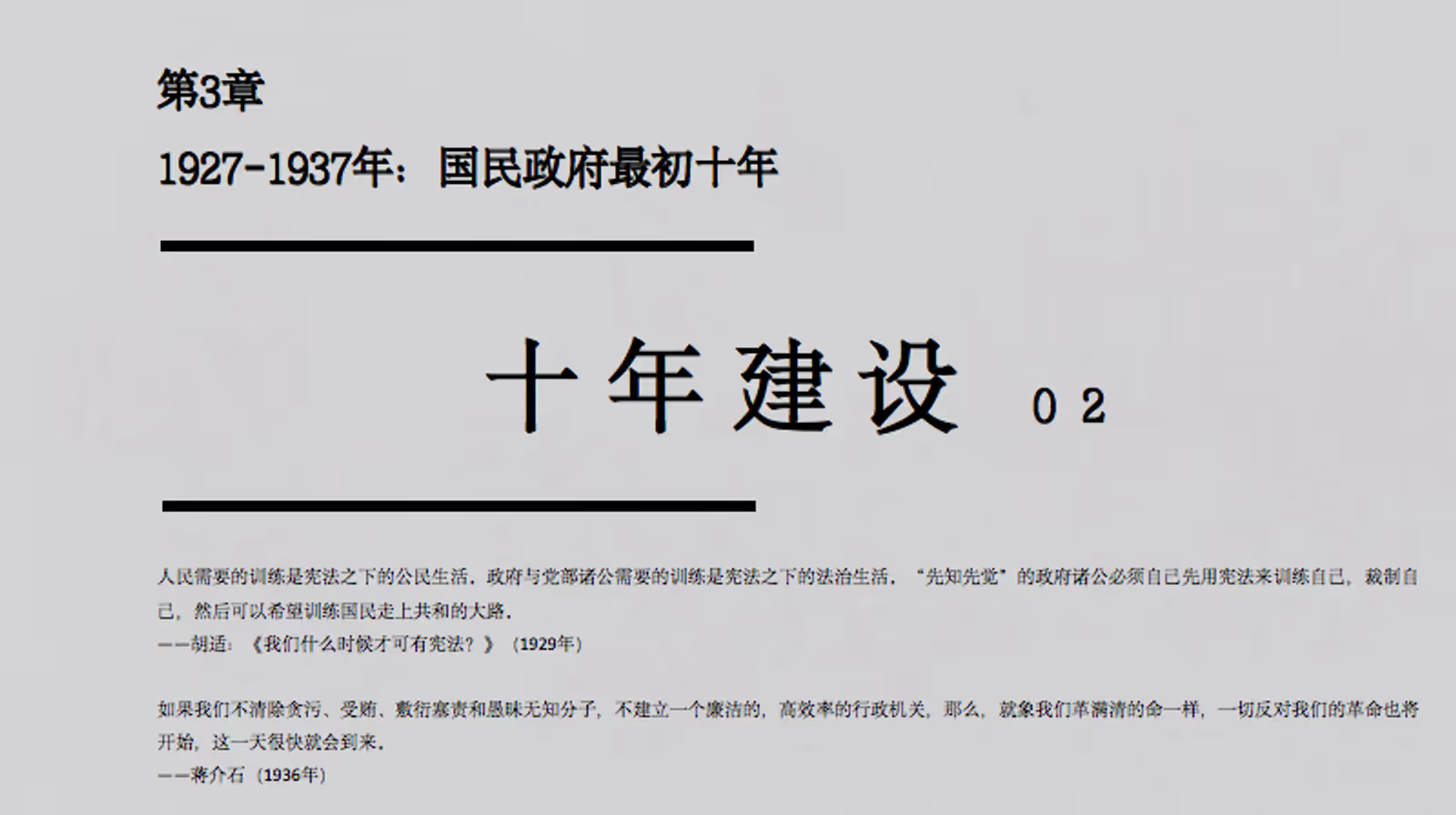
在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实现了币制的改革: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改变了白银由于地区、重量和成色导致的差异与波动,7月1日,新银元开始流通,尽管当初推行这个金融改革遭遇了国际市场银价的飙升导致白银迅速流向国外以致引发了通货膨胀、高利率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1935年11月,法币(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开始流通,中国的社会经济第一次开始在统一的货币制度下运转,进而白银开始集中于中央政府——尽管这一年储存的白银288,000,000元只是1934年4月的三分之一,以后人们认识到的意义是,法币的流通的确为南京政府统一全国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这一年,美国不仅派出了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还给予了10亿元的经济援助。
在现代化建设上,统一度量衡标准单位为实现机械化发展和日常经济生活提供了条件,同时,从1936年3月发表《重工业三年计划》开始,引进国外的资本与技术成为可能。涉及工业、矿产、农业、水利新修等领域,都有基础性的数字增长和结构性的变化。无论从主权、军事还是经济上讲,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自行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在“安内攘外”的几年里,国民政府完成了公路从之前的1000多公里发展到16000公里,铁路从之前的8000公里增至13000公里以及11条空中航线与47个航空港的建设。在一些主要的城市,通讯(市内、长途以及国际)的基础网络基本建成,邮政权全部收回,并有建设性的发展,到了1936年,全国邮政局已经有了14000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下,朱家骅建议的中国现代国家应该具备的义务教育有了实施。高等教育、中小学普及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有了较为平衡的细分,即便处于民族危亡日益紧要的关头,学校的数量以及教育的师资仍然得到增长,1937年,全国有中学超过2000所,师范1000多所,职业学校远远地超过300所,服务于现代城市的社会福利事业例如卫生与医疗机构的建设,开始有了从现代医院到诊所不同层级的机构出现。
不过,既然是国民党控制着国民政府的运行,而军事与政治的目标是国民党的“训政”基础,这样,国民政府事实上没有完全将工商业资本家看成一股在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力量,而是当作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获得财政收入的来源,并严格限制着私人拥有更多的工厂、矿山以及土地资源,以至于民族经济并没有完全进入自由经济的轨道,只有银行家可以通过特殊的关系与交易获得稳固的势力范围,只要他们愿意主动地借钱给国民政府。结果,国民政府操纵国民经济仍然是实行一种人们早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就看得很清楚的国家资本主义:强调用国家权力建立企业,避免让大企业落入私人与外商手中,不让私人资本主义和大富豪阶级出现,这样,商业和企业必须成为国家的财富,国家甚至将市场公司国有化——例如1932年的南京政府将轮船招商局国有化。这样的指导思想不可避免会将各种负担加在私营资本家与个体企业,例如私人企业向银行的借款利息很高(15-20%的利息),一些国产商品需要支付的进口原材料关税与进口同样产品本身的关税几乎一样,这大大地阻碍了私人企业的发展。
十年时期的国民建设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当1935年国民党宣布“赤匪已经消灭”时,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也获得了一半的实现。一个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以致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之大市场”。就在1935年1月23日,日本广田外相就对华政策方面发表了“不威胁不侵略”的讲话,前提是中国必须彻底取缔排日运动,2月13日,广田外相与日本驻上海商务官横竹平太郎还发表了中日经济提携大纲,涉及到两国交换民间实业视察团、援助中国农业、增加中国商品进口和援助上海银行[1]。国民党呼应了这样的要求与对两国之间和平的期待,蒋介石、汪精卫与孙科都发表了争取与日方合作的积极表态,蒋介石明确接受并推行日方“取缔排日运动”,其中的目的还包括根除中共的抗日据点。不过,知识界对日本方面的表态几乎没有信任,例如傅斯年就认为“中日经济提携”不过是“灭亡中国的捷径”;胡适怀疑说:“只要‘满洲国’存在,中日两国关系就难于真正好转”[2]。可以想象,日方的建议与国民政府不得已的呼应导致了中国知识界和民族主义者的反感,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敏感在年底受日军支持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5日)和“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18日)的成立似乎得到证实[3]。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实施投降与不抵抗策略。1935年最后一个月,中共河北省委利用学生的民族主义激情,领导并组织了声势浩大、让国民政府极为难堪的学生运动。12月9日,北平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数千大中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政府终止华北自治政府的成立,尽快停止内战,共同对外。在递交给政府的请愿书里,学生们强调的是出版、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是结束政治上的压制。12月16日,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超过1万名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阻止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这个被称之为“12.9学生运动”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清华大学救国会高全国民众书》(蒋南翔起草)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名言传遍全国,很快,学生们的愤怒与激情燃烧到天津、 广州 、 武汉 、 南京 、 上海 各个城市。各种救亡团体与民间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针对这个民族危亡时期的评估,人们反复指责的是政府的军警用高压水龙头、扑打以及逮捕、镇压学生在街头的爱国主义行动。而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确也在想尽一切办法与策略尽可能地拖延正面抵抗,争取时间:只要可能,涉及军事、经济、金融、教育的建设都在继续。蒋介石早在1928年5月因为“济南事件”就受到了普遍的质疑[4],但正如蒋介石这年在国民党五大讲演中的表述:“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的确,国民政府第一个十年承受了巨大的历史包袱:大多数民众对满清的生活比民国的教导更为熟悉,民众的现代意识需要普遍启蒙;地方军事将领从来就没有全局意识,尽管他们中间的部分人会利用现实的问题为自己的言行做辩护,“军事责任义务”显然消耗了国民政府大量的资源;党内派系永远不能终止,在如何理解孙中山的遗教,以及在党内权力究竟是更多的集中还是实施民主始终争论不休,以致不断地影响着中央的决策与政治安排;在国民党看来始终在捣乱的中共不断举着看上去更加符合人们理想的旗帜以致不能够让民国政府安宁,军事围剿消耗着国家大量资源;加上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的财政、经济以及民族心理的破坏与打击,任何一个执政党及其领袖在面临这样混乱与复杂的局面时,都只能是伤透脑筋并在其工作中表现出破绽百出,让他的人民不能满意,以致使社会局面始终不得稳定。然而,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仍然坚持着让这个国家尽可能地“现代化”。的确,蒋介石不再相信共产主义者的合作,这也是为什么蒋介石在将苏联教导军官赶走之后,就与德国在军事、工业和文化上进行合作——这样的企图和努力直至抗战即将全面爆发时才结束——的原因。
没有人愿意,但事实也只能是如此:基于国民政府完成北伐之后的客观历史条件,在从接手混乱到建立秩序这样一个过程中,任何人、任何政党和组织试图获得政治清廉、社会安宁、秩序和谐以及全体人民兴高采烈的政治结果的愿望,都是办不到的。而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公职人员平庸无所作为,党内的宗派主义、对党外异见人士的迫害和对言论自由的严重侵犯,也同样是直到今天的大陆也存在的问题。
很清楚的是,正是国民政府在这十年努力的成绩,让大多数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趋势不可逆转;在国家面临深重的危机时,随着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日趋明朗,浓厚的民族主义空气也容忍了国民党治下的弊政和问题。事实上,在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在全国多数人的眼中的确是一个牵涉到国家与个人命运,因而被强烈地依赖的民族领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形象获得了空前的认同。无论如何,蒋介石在这十年里将党内派系矛盾控制在最低限度,在不同规模的战事(无论是对军阀还是中共)没有终止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领导国民政府推进现代化的建设。归纳地说,十年建设不仅是之后全面抗战能够获得胜利的条件,也是留给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遗产。
注释:
[1] 《日驻沪商务官昨抵东京谒广田》,1935年2月12日《中央日报》。
[2] 胡适:《中日提携,答客问》,《独立评论》143号,1935年3月25日,第2-3页。
[3]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1月25日)由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 殷汝耕 等人在日本人的操办下成立,1935年12月25日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同时发表《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组织大纲》。政府所在地初为 通州 (1937年8月,由通州移驻唐山),统治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统辖约六百万人口。财政收入占河北省的22%,1938年2月1日并入北平王克敏组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主要诉求为“华北自治”、“防共缓冲自治”,实为日本对中国进一步的吞噬。基于与日本商人的合作, 殷汝耕 政权对 天津海关 的收入与国民政府的贸易造成冲击,影响到不少工厂倒闭和店铺停业,物价上涨以及失业人数的增加。
1935年,日本提出的“华北五省自治”,指望通过使“华北问题特殊化”控制更多的范围。之前通过《 秦土协定 》(6月27日)和《 何梅协定 》(7月6日),日本实现了对冀察两省的觊觎,接着,日本人向 何应钦 要求华北自治。在日本的逼迫下,国民政府改变了华北的行政体制,于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 员会( 管理范围 涉及 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 )。 任命二十九军军长 宋哲元 为委员长,宋拥有独立的人事、财政、税务权力。日本将这个南京政府的地方政权视为自治机构。日本的目的是在满洲国与中华民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加强满洲国的安全,并为之后的进一步入侵提供条件。在国民政府看来,这只是尽量避免正面冲突的权宜之计。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1年零7个月。
[4] 济南事件又称济南惨案(Jinan Massacre)。1928年4月, 蒋介石 的北伐军队挺进北方,5月初在济南受到日军阻扰——日本人基于1919年从德国人手中接管的特权,试图阻扰北伐。日军对国民政府的职员和国民革命军军人以及中国民众实施屠杀(超过17000人被屠杀,数千人受伤)。最终,考虑到了尽量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导致北伐力量的削弱甚至有可能因为军事能力的不足使得军事行动完全失败,蒋介石派出的外交部长与日本签署了停止冲突的协议,这一遭受屈辱的举措受到国内普遍的批评和愤怒的指责。不过之后的下半月,蒋介石的北伐军消灭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并将张作霖逼出北京。